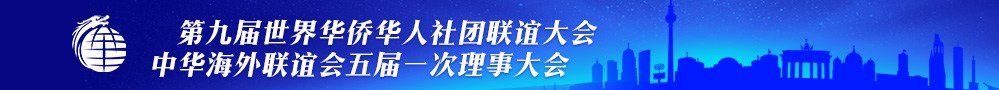Archigram作品
建筑团体Archigram通过作品向观众传达:建筑关乎改变、不同的可能性和选择。该团体由沃伦·查克、彼得·库克、丹尼斯·克朗普顿、大卫·格林、朗·赫伦和迈克·韦伯组成,其活动横跨出版、教育与展览等领域,于196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在当时被建筑界主流视为“搅局者”。Archigram致力探索建筑如何配合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日新月异的科技、以及不断翻新的流行文化。他们创造的独特视觉表达形式,对流行文化以及影响元素的运用等,都以一种轻盈的方式挑衅着城市系统的缔造者,呼唤城市新的生命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图像时代,他们的实验依然具有长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Archigram作品

Archigram作品
在论坛上,迈克·韦伯谈到了建筑与绘画的关系,“你应该把自己当成是占据空间的个体,让自己融入绘画当中,然后才能去感受,想像如果是住在画当中的居民,你如何和周遭的环境发生关系。”彼得·库克则认为,漫画能够描述出居住于建筑中的人的心里状态,与此同时,身为实验建筑师,并非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与他人的及交流中吸取经验。“总结来说,你必须要往外看,而不是只盯着自己的东西。”
《798》
绘造社第一个作品完全就是复制了Archigram当时的一个做法,也是一个出版物,就是《一点儿北京》,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建筑图画了北京几个我们特别喜欢的地区。这些图看上去像一个插画,但是背后的原则是按照制图原则来做的,怎么切开建筑,怎么移动,怎么平行移动这些元素。建筑部分用制图软件,人物和植物是手绘的,后来我们逐渐放弃了手绘。这本书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我们继续用建筑图的方式来介入建筑。当然一开始我们其实确实没有委托,这是和张永和老师合作完成的一部图像小说,我们对张老师进行了采访,把采访变成故事脚本,以图像小说的形式进行呈现。这个图像小说的背景是张永和早年的设计“线性城市”,他构想了13个特别狭长的建筑,每个建筑功能不同,我们在电脑里面把它的图纸变成空间,组成一个线性城市。创作完以后,我觉得比起叙事,更重要的是图和文字结合起来产生那种氛围,最终的“脚本”描述了线性城市里的生活,都是日常性的东西。我们主要想传达或者表现一种氛围,荒诞,复古,你永远回不去,但是好像又特别吸引你。
绘造社与张永和的合作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一开始我们觉得建筑图只是一种尝试,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以图像或者媒介的方式介入建筑学,我觉得还是很有空间的。
《南锣鼓巷组画之过客》
我想再谈谈建筑图。我相信大多数建筑师把建筑图当成一种工具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建筑图不仅仅是工具,其实就是一种艺术。Archigram所有的图都是用尺子、圆规、模板来画,非常精准,似乎也很僵硬。木头对刀的限制,尺规对灵活性的限制,让他们的图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机械美,这种美是其他的绘图方式很难出现的,我认为这是建筑制图美的最高境界。
吉首美术馆
对我来说时间是延续的,在Archigram的视觉呈现里,从来没有传统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传统和今天是共存的,历史是今天的一部分。这就是步行桥,人能在这里休息,在这买卖东西。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作为建筑师,既然想让行人可以看到艺术,那仅仅把美术馆放在这个桥上面,还是不够的,如果它不进入美术馆,不还是看不见吗?所以我们就想了一招,在美术馆的地板上开了两个大天窗:可能就是买菜的路上,一抬头,一不留神看到了一张画。我们想创造的是在城市中,为那些恰恰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创造和艺术相遇的机会。
西村大院 鸟瞰图
因为不知道什么商家会进驻,这个房子就变成通用空间的设计,所以设计没有那种强烈的立面,所有的立面上都是用玻璃,但是还是给它做了一些隐形的设计:底层高一些,二层也高,三四层低一些,顶层因为有屋顶,又高一些,玻璃的划分其实已经暗含了怎么搭夹层。层层叠叠的跑道里可以看到人们在开会或是打麻将。这个建筑给我的经验就是,你准备好空间,如果它尺度合适,就会发生相应的事件,有很多设计未必要用很物质的方法来呈现。
文里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
这是最近完成的文里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泥鳅钻豆腐”是这个项目的关键词之一。整个项目就像插接进老的建筑一样。这里有城隍庙和文庙两大古迹,还有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房子。这个设计就是见缝插针,根据那些古近代建筑所需要的保护距离和必要的防火间隙,在那里面绕来绕去,东钻西钻,有些是文物保护的规定,有些是消防规范,就是这么得出来的一个轮廓。我们要在里面植入新的功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都看作历史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段。“当代”介入它的时候,过不了多少年也会成为一个片段。
《浮游之岛-世贸重建》
我在耶鲁留学最后一个学期的作业就是关于城市的。我的作业像一个梦境,想了很多的办法去表达对“9·11”事件的想法。我就画了这个图,这个草图就像在天空飘着的云,是横向展开的,有非常大的尺度。我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草图,我觉得它是一个有野心的、对固有的现代主义城市有很强破坏力的草图,这受到了很多理想主义色彩的建筑绘画,也包括Archigram草图的影响。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到大部分的这种现代主义建筑的归宿都是成为权力资本的象征物、纪念碑,他们冲突了天空、高度去竞争。我就想表达一种解脱——我设计了这么一个水平状的建筑,它飘浮在所有的摩天楼之上,它的顶部有公园、水面这种自然的因素。我觉得我没有去重复那些对古典现代主义城市的巩固或者说纪念,而是想超越它,这个精神好像是受到了Archigram时代,很多年轻建筑学人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气质的影响。
胡同泡泡32号
回到北京以后,我也做了一个“空想”式的作品,叫“北京2050”,这里面就是谈北京的城市问题,里面包含了三个不同的课题,其中一个把2002年的想法加以发展,对我来说是一个针对北京的乌托邦式试验。第二个关于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改造,我设想这些院子里可以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这些小泡会在院落的角落长出来,里面可能是一些新的功能,四合院里没有的功能,以至于让生活在老城里的人还能融入到当代的生活,后来整个想法被一个业主看到并加以实现了。我们的想法是“泡泡”能通过自己的材质反射周边,融入周边的环境,让自己消失在古典的环境里。新和旧在这个项目可以共存,这个项目有它的英雄主义色彩,但是又跟那种特别宏大的城市巨尺度改造不一样,它是一个针灸式的改造。“2050”里面还有一个项目,希望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一个森林公园:它更像一种社会抱负,把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空旷的混凝土空间变成一个人文的、绿色的开放城市客厅。
2017年深港双年展,南头古城
第二个要讲的是“城上造城”,由于我对现代主义的城市深度怀疑,所以我们一直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在现代城市基础上,再叠加一层新的城市空间和生活,这是我们一直在探索,让新的房子像插件一样插在老的社区里面,让新与旧能够共生。我们最近很成功把一个城中村“扣”在一个上次上,使人的尺度和传统的购物中心有一个组合。这个房子既可以当办公,又可以居住,层高是可以调整的,而且每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深圳CBD中轴线
我们一直在讲旧城更新,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改造的是我们建的新城。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深圳的城市中心已经形成了很多年,它也代表着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CBD模式,我们思考的是,它在现有基础上有没有可能编写一层新的城市生活,在原有单调乏味的城市里是不是能够激活和产生新的可能性?CBD中轴线集中体现了效率、速度、交通为上的发展模式,但是在今天它的活力受到了影响。早在十年前,我们和OMA合作做了城市的研究,想把整个城市中心重新连接起来,我们采取了一个连环的做法,连的不只是地上,同时还有地下高铁站、城铁站,所有的商业。最近,我们希望在这个层面上再增加艺术家、建筑师、新的机构、新的创意等。新城改造计划需要更多的建筑师和各方面的专业人士。